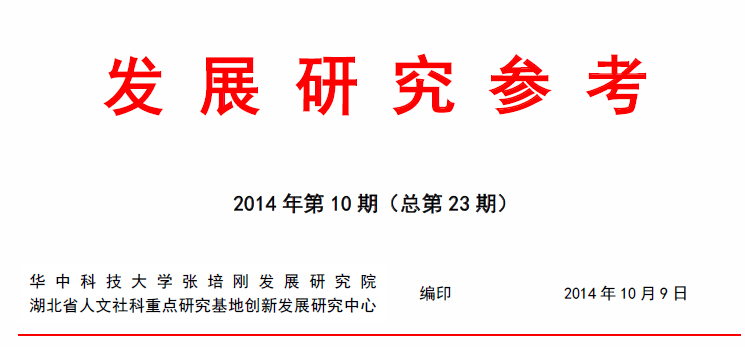
中国产业政策的反思
—----基于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视角
张建华 周凤秀
一、 引言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各产业的整体平衡及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称。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许多后起国家为赶超发达国家,谋求经济跨越式发展,均采取了“适宜的”产业政策,并快速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战略性产业。
然而,对于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有何作用,学术界存在争议。一派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对促进产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Williams等人(1993)认为,产业政策,是为了克服市场竞争缺陷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总称。政府实施产业政策之目的是拟通过产业政策来辅助协调经济发展。对于产业政策的作用,Ito(1992)认为,产业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显著提升了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张夏准(2002)等则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Robinson(2009)指出,产业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且作用大小因不同国家和采用的政策内容而有所不同。Tilman(2011)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是考虑是否采用产业政策,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产业政策。
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产业政策是无效率并且是损害产业发展的。如日本新古典主义学派就认为,实施产业政策损害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政策终将失败。Noland(1993)也认为,产业政策的实施,并未使得资源流向新兴产业,而是流向成熟的、具有政治背景的产业。即使国家实施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体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对企业效率和政策效果的研究后发现,产业政策没有达到促进产业优化的目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调整, 经济发展总量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质量却存在一些问题,如过度依赖重工业和投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都还相对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从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经验事实来看,我们认为,中国有必要实施产业政策,但其效果取决于政策方式,也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构架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试图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政策演变探讨两者的关系,从当前经济运行绩效反思产业政策的成效,并对未来政策走势提出思考。
二、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与产业政策演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农业、轻工业和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为1992~1999年制造业及出口快速增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为2000以后中国进入重新重工业化阶段阶段。
(一)农业、轻工业和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工业化以农业、轻工业和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为主要特征,其工业化战略可概括为: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适当控制重工业。主要成就表现为:1.农业和服务业快速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开始协调发展; 2.轻工业发展迅速,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趋于协调。3.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加强和经济快速增长。此外,这一时工业化成就还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1991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和总产值分别是1978年的12倍和13倍;二是外向型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4.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91年的1357亿美元,外资实际利用额增加3倍;三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1979-199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在9%以上。
(二)制造业及出口快速增长时期
这一时期采取以全面市场经济为主要配置方式的工业化道路,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对外开放,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为主要战略举措。该时期工业化使得中国经济继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轻工业和出口加工工业发展迅猛,三次产业进一步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进一步演进。在工业内部,轻工业的发展略快于重工业,轻重工业总产值之比基本稳定在1∶1。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三)中国重新重工业化阶段(2000年+)
从2000年开始,中国工业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工业化中期的重工业化阶段,这是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时期,目前尚未完成。由于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曾经重点发展过重工业,现在再次发展重工业,所以称之为“重新重工业化”或“二次重工业化”。这一时期工业化的主要特点为:重工业增长速度加快和比重提高。出现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从1999年的53.8%猛升至2005年的67.6%,超过早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记录。到2012年重工业比重已经达到71.8%,重工业利润占全部工业利润的72%以上。
三次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第一产业到2012年其比重已经降至10%,第二产业比重在经历了2000~2006年的短暂上升后也开始缓慢下降,从2006年的最高值48.6%下降至2012年的45.3%,第三产业比重则呈持续上升趋势,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按照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中国工业化正处在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关键时期。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产业政策发展也对应经历了阶段性变化:
自1978年推进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 虽然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 但政府一直致力于调整计划经济体制下过于扭曲的产业结构。这一时期中央通过强制性政策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其目的在于迅速恢复生产和提高人民收入,使劳动力流向密集型产业,为发挥比较优势打下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期, 中国正式制定产业政策。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 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推动总体产业发展, 即是从宏观方面来引导产业的运行,虽然产业政策的作用较为有限但基本不存在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政干预。1994年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第一个正式的产业政策。此后专项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0年以来至今, 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促进重点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为主, 产业政策不断细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制定针对总体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外, 针对重点产业的产业政策不断增多。例如,《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等政策, 分别对国家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产业目录提出明确要求,并确定具体配套政策措施, 希望通过产业政策促进支柱产业发展, 并调控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三、从经济发展质量反思中国产业政策的特征与效果
伴随市场经济体系构建,中国的产业政策从宏观战略层面开始进入中观和微观层面,并实施了更具有针对性的专门化产业政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广泛运用产业政策工具,引导企业行为和经济发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优化。
然后,产业政策的这种新变化却加重了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问题,诸如:产业过剩问题愈演愈烈,产业布局严重失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巨大,大多数产业垂直分工处于弱势地位,研发、营销、资源整合等核心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普遍欠缺;低端产业规模大,制造业大而不强;本土产业起步晚、竞争力不强,在外部经济的冲击下,不能形成真正的优势产业;同时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如国际经济不平衡、自然资源短缺、贸易保护、环境污染严重等巨大压力。
究其原因,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当前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密切相关:
一是重视支持大企业发展,主要表现为保护和扶持在位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21世纪以来,“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实施重点产业部门大企业集团战略、提高中国工业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实施这类政策的理由往往是“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提高市场集中度,避免过度竞争”等。其理论依据一般是“市场失灵”、“经济发展、赶超需要”等。相关政策部门往往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确定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时,偏向于在位大型企业,对新进入中小企业发展进行限制。总的来说,并未改变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不协调。如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一直将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协作作为主要目标,而忽视了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作用在于“协调竞争秩序与规模经济的关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抑制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和防止过度竞争。上世纪80年代,虽然当时的经济工作重点还是促进供不应求产业发展,但中国产业政策同时也在控制或限制一些产业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抑制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2004年以来,抑制产能过剩一直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对被列入产能过剩行列的行业,原则上不再批准扩大产能的项目;对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不按规定程序审批或核准的项目,一律不得通过企业债、IPO等方式进行融资等。
三是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鉴于中国绝大部分产业的集中度很低,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鼓励提高集中度。近年来,从“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到“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毫无例外地提出了要“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在这种政策环境及其导向下,一些地区部分行业格局出现重大改变,争议颇大。
四是鼓励技术引进。中国的产业技术政策既是产业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技术政策的组成部分,几乎涉及所有产业,因此也可看作是整个国家的技术政策,其重点随产业发展及环境变化而动态调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希望通过扩大外资引入,以市场换技术,但效果不佳。
五是对微观经济直接实施行政干预。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强调利用市场机制,但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部门利益和寻租动机等,使其具有过于强烈直接干预市场的特征。具体表现为针对单个行业的产业政策数量显著增加,政策内容更细化、政策措施更具体。广泛地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和限制竞争,导致产业结构、重点企业、技术路线等有时并非由市场主体自身行为决定,而是政府主导形成。
六是产业政策体系具有多层级性。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其辖域)均可制定、实施影响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实际上,不同主体的层次性、利益和目标上的不一致性,常常导致产业政策的扭曲或选择性解读。产业政策体系的多层级和产业政策多主体的性质,使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多个行为主体的影响与制约,利益关系复杂。这往往也导致政策效果难如人意,甚至事与愿违。
中国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估
中国的产业政策的作用和效果有限,只有部分产业政策在特定时期和阶段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许多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反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能力的增强。
对政府高度关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存在诸多争议。治理产能过剩政策对一些部门长期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判断有待商榷,对超越环保等功能性监管之外限制投资、强制退出是否合理也存在诸多不同看法。
扶大抑小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中国产业政策显性的规模化导向加上隐性的所有制歧视,导致资源过多地流向效率并不具优势的国有大企业;而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不仅难以得到支持,反而受到诸多制约。中国企业一般倾向于外延式扩张快速做大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而相对忽视内涵式做强,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等方面的关注和投入相对不足等,加剧了经济效率受损和创新动力弱化等问题。
中国产业政策及其经常性的直接行政干预已严重影响了企业创新、升级和转型等长期行为。中国的企业家不得不经常面对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不确定性,企业经营决策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导致企业没有安全感、对未来缺乏信心,一些企业家出现移民浪潮和投机行为。由于直接干预,产业政策抑制了市场竞争学习机制和筛选机制发挥作用,不仅难以避免因集中度低和过度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效率损失。
当前激励性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为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性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与原来支持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相互叠加、嵌套,构成了庞大繁复的政策体系。
第一,政策激励面过宽,导致政策着力点和重点不够突出。现行政策就激励对象而言,涉及到科技人才、企业家及经营管理人才、研发机构、创业企业、上市公司、投融资机构、企业孵化器、产业园区等方面。这些政策多而泛、广而散,必然难以形成推动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合力。
第二,功能界限模糊。现行激励政策手段主要包括财政、税收与信贷。从理论上说,各种财政手段应有明确的功能与司职范围,作用于产业发展链条的不同阶段,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政策体系。但在各种财政手段的实际应用与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功能界限模糊、职责范围不清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财政经常性无偿投入与专项资助领域存在着较多交叉重叠资助情况。
第三,激励对象错位。支持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和重点应是激励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激励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大力发展高科技创业企业。从对现行优惠政策看,大多数政策是以企业为激励对象,而现有企业所从事的产业往往是已形成规模的产业,并不具备新兴产业的特质。
为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项资金、基金项目,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目前这些基金大都是沿用行政管理运作模式,普遍存在约束监督不力,政府财政投入流失和浪费,甚至可能导致腐败。
四、中国产业政策的未来取向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行政指挥作用和直接安排能力显著地降低了。但是,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一方面政府希望行政力量能够在促进产业快速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权力意识和利益冲动仍然强烈存在,并往往借助于产业政策的形式来表达权力和实现利益。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中国产业政策形成了一个复杂体系。
我们建议,中国应该极大地简化产业政策,尽量减少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更多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来选择和培育支柱产业、规定和控制产业规模、设定和提高产业集中度。中国的产业政策需要更加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尽可能避免用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
未来的产业政策首先应定位于致力创造“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其次,产业政策应该强化社会性规制,在控制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提高安全生产标准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组织的重要工程和重大项目对一些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未来政策重点包括:
1、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所谓功能性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不划定优先发展某种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而是为全部产业或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合理、软硬环境优异的竞争平台。因此,应摒弃具有国家强制干预色彩的产业政策,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完善激励性产业政策, 核心是遵循新兴产业发展规律,遵循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激励政策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2、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竞争手段,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最有效手段,且技术创新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增强企业创新的活力,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同时,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创造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体制环境,使产业的资本密集、劳动密集结构适应我国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现状,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优势。
3、重视环境保护。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政府应主动施加干预,处理好与企业利益及环保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改进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将环境指标列入政绩考核,促使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本文为作者提交2014年 9月18-21日中德经济研讨会(Sino-German Joint Conference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Growth i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fter the Debt Crisis” 发言的中文版提要,也是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基于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12&zd04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Williams S L. Jap anises industrial policy:What is it, and has it worked [J].Canada-United States Law Journal,1993(19):79-92.
[2] Ito. T.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92.
[3] James A. Robinson.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09 World Bank ABCDE conference in Seoul June,22-24.
[4] Altenburg, Tilman (2011).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verview and lessons from seven country cases. Bonn: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Retrieved 25 August 2012.
[5] Nolan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Jap an’s trade specialization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3,75(2):241-248.
[6] Anne O. Krueger, Baran Tuncer.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Repl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84.
[7] Richard Beason, David E. Weinstein.Economies of Scale, and Targeting in Japan (1955-1990)[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78.
[8] Chang,Ha-Joon,2004.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ing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9] Cimoli,Mario,Giovanni Dosi,and Joseph E. Stiglitz,eds. ,2009.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Dasgupta,Partha,and Joseph Stieglitz,1988.“Learning - by - Doing,Marke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i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0( 2) : 246 - 68.
[11] The Economist,2010. “The Global revival of Industrial Policy: Picking Winners,Saving Losers. ”The Economist.August 7th : 19 - 21.
[12] Evans,Peter,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 Hudson,Michael,2010. 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 - 1914: The Neglected Americ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Kansas Cit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ong Term Economic Trends.
[14] Irfanul Haque,2007. Rethinking Industrial Policy.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UNCTAD) ,Discussion Papers,No. 183.
[15] Johnson,Chalmers,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Kang,David C. ,2002.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 Kohli,Atul,2004. State - 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 Krugman,Paul R., 1983.“Targeted Industrial Policies: Theory and Evidence. ”In Marvin Duncan and Marla
[19] Lee,Simon,2010.“Necessity as the Mother of Intervention: The Industrial Policy Debate in England. ”Local Economy. 25( 8) : 622 - 30.
[20] Norton,R. D., 1986.“Industrial Policy and American Renewa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1) : 1 -40.
[21] OECD,2013.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3: Industrial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2] Rodrick,Dani,2009.“Industrial Policy: Don't Ask Why,Ask How. ”Middle East Development Journal 1( 1) : 1 - 29.
[23] Sbragia,Alberta M. ,1996. Debt Wish: Entrepreneurial Cities,U. S. Federalism,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4] Schmitz,Hubert,2007.“Reducing Complexity in the Industrial Policy Debat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5( 4) : 417 - 28.
[25] Vestal,James,1993. Planning for Change: Industrial Policy and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1945- 1990. Oxford: Clarendon.
责任编辑:范红忠 黄 莉
编辑部通讯地址: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大楼506 (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037号)
邮政编码:430074 电话、传真:(027)87542253 MAIL:hustjy506@163.com
研究院网址: http://cids.hust.edu.cn/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http://cids.hust.edu.cn/cids/

